张倬,电视剧封神英雄里面的杨戬?
封神英雄榜大哪吒张倬(zhuó)闻殷郊来子旸(yáng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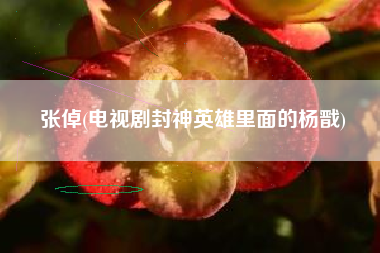
雍正是否吕四娘所害?
我是旅行者说文史,这个总是我来回答!关注我,更多文史知识与你分享!
清雍正时"吕留良案″冤吗?我们在分析吕氏家族到底冤不冤之前,先来看一下,吕留良案是如何案发的。
吕氏一族灭于雍正,倒不如说灭于曾静这个无耻文人之手公元1728年,即雍正六年的一天,川陕总督岳钟琪在打道回府的路上,收到一封信。岳钟琪拿过来一看,只见这封信的封面写着“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”,他马上就感觉到气味有些不对头。所谓“无主游民”,就是不臣服于当局,不承认清政府的统治,那么,这封信的内容可想而知。果然,岳钟琪把信拆开仔细看完以后,吓得不禁大惊失色,浑身直冒冷汗。他立即下令,将奉曾静之命前来送书的张熙关押了起来。
原来,信中列举了雍正皇帝的十大罪状:谋父、逼母、弑兄、屠弟、贪财、好杀、酗酒、淫色、诛忠,任控。
这十条罪状,囊括了雍正皇帝继位以后所有的重大政治事件,也可以说是社会上流传的对雍正皇帝进行攻击的总归纳,把雍正皇帝描绘成了一个谋皇篡位的伪皇帝、不讲人论的败类,如果属实,那雍正当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了。
信中还说,自雍正皇帝继位以来,湖南、湖北多地连续几年发生了大水灾;江苏、四川、广东多地更是不时传来旱灾。普天之下,山体崩塌、河水枯竭、天昏地暗,堆起来的尸体把道路都截断了,这是上天对雍正皇帝的不满。只要岳将军举旗一呼,天下百姓定会响应,到时候驱逐满人,恢复中华就是分分钟钟的事。
那么,民间的反清力量又为什么要请岳钟琪出面当天下兵马的领头人呢?这是因为,这些反清力量认为,首先,岳钟琪贵为川陕总督,手握重兵,由岳钟琪领头起事,定然一呼百应;其次,据说南宋名将岳飞死后,他的子孙死的死,流放的流放,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,就有一支逃到甘肃定居了下来,这就是岳钟琪的先祖。岳飞为了抗金,不惜身死,而满清又跟金国同宗同源,作为岳飞的后人,岳钟琪一定会反对清朝皇帝的残酷统治。
通过后来的事实证明,这些只会纸上谈兵的迂腐文人,夸夸其谈还可以,真遇到有损自己利益的时候,只要把错误一股脑都推给他人。岳钟琪虽然是一名武将,但他也不会被曾静的几句胡言乱语糊弄了。于是,他给雍正皇帝上了一道密折,请求将张熙押往北京,请皇帝亲自来审这个案子。
也许是要考验岳钟琪是否对清廷忠心不二,也许是要通过岳钟琪公开处理这件案子摆出自己的立场,雍正皇帝作出了批示,要求岳钟琪全权审查此案,并且不要重刑逼供。
岳钟琪接到皇帝的批示以后,就将张熙偷偷放了出去,把他当做上宾一样招待,并夸奖他是一条硬汉子。岳钟琪说,自从雍正皇帝的近臣年羹尧死后,自己就有了反意,只不过皇帝暗中派了不少人来监视自己,处境十分的危险,之所以先前扣押张熙,就是想验证一下,张熙是不是皇帝派来试探自己的。岳钟琪说,现在终于知道张熙是真心反对满清的,希望张熙能当自己的老师,共举义旗,推翻满清,光复汉人的江山。
张熙听了岳钟琪的话,完全解除了对他的戒备,激动地说出了如何奉老师曾静之命前来投书的经过给岳钟琪听。岳钟琪取得了张熙的重要口供,立刻露出了真实面目,大笑一声,把张熙重新投入了监牢,把案情上报给了雍正皇帝。
原来,张熙的老师曾静是湖南永兴(今湖南永兴县大布江乡较头村蒲箕塘)人,生于康熙十八年,是一个屡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有考中的落魄书生,平时靠在乡野开设私塾勉强糊口。张熙25岁的时候就跟着曾静读书。
康熙年间,浙江有一个理学大儒叫吕留良,一生拒不入仕,隐居乡里编书著作,大讲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,反对满清的统治。由于吕留良的这些观点大都写于他的日记、诗词、文集之中,并没有公开发行,所以,一直到吕留良去世也没有被清朝统治者所发现。
曾静认为,吕留良隐居乡野跟自己在乡野授教一样,都是反对清朝统治者的。只不过,他不愿意承认,吕留良是真的大儒,康熙年间,清政府数次请他出来做官而不去,为此还剃度当了和尚;而曾静就是一个学渣,考了一辈子科举,到五十来岁连个秀才都没中。曾静派人到了浙江,找到吕留良的后人,表示他们对吕留良是多么崇拜,吕留良就是照亮他们人生一盏的明灯。一番忽悠之后,吕留良的后人就将吕留良饱含民族情绪的遗作全部交给了曾静,却不料,就是曾静这个无耻文人,在吕留良死了四十多年后,给吕氏家庭带来了滔天大祸。
曾静到案以后,就把一切罪行都推到了吕留良身上,反正吕留良死了快五十年了,也跑不出来跟他对质。曾静说,他就是乡下一个教学先生,一辈子也没有看过几本书。自己的这些反动思想全部来源于吕留良。现在,他知道错了,只要能留下自己一条命,愿望写一篇《大义觉迷录》向天下的读书人宣讲,来讴歌雍正皇帝的丰功伟绩。
于是,雍正皇帝对曾静师徒展示了令人不可思议的仁慈,当场就释放了曾静师徒,并任命曾静为全国道德模范宣讲团团长,巡视全国,向读书人宣讲。曾静所到之处,受到了地方官员的高度重视和礼遇。曾静把一个无耻文人的嘴脸演绎得淋漓尽致。
雍正皇帝对吕留良的家人和师生却采取了极其残酷的处理方法。吕留良及其子吕葆中已去世多年,仍然被劈棺戳尸,枭首未众;吕留良的众孙辈及学生全部被发配到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隶;吕留良的全部家产没收充官,作为浙江工程费用。
雍正皇帝难道真的死于吕留良后人吕四娘之手吗?吕家的悲惨遭遇,受到了很多的人同情。其中流传最广的是,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因为在安徽乳母家中而逃过一劫。吕四娘听说吕氏一族惨遭灭门,便写下“不杀雍正,死不瞑目”八个大字。为报家仇,吕四娘下江南拜大侠甘凤池为师,苦学本领。学成之后,吕四娘只身入京,混入皇宫,杀死了雍正皇帝,并割下了雍正皇帝的首级,用来祭奠自己的先人。
这个传说虽然说流传甚广,但真实性不高。雍正皇帝当时查办吕留良之案时,属于高度机密,吕氏一族不可能有漏网之鱼。另外,甘凤池倒是历史上一个知名人物,但是自雍正七年,被李卫擒后,就归服了李卫,并没有授徒吕四娘之说。
吕留良案的罪魁祸首曾静,虽然在雍正朝侥幸躲过了杀身之祸,但是到了乾隆皇帝继位以后,他就不顾雍正皇帝生前保全曾静、张熙的叮嘱,下令湖广巡抚将曾静、张熙押解到了北京城,凌迟处死,并将与此案有关的《大义觉迷录》及吕氏著作全部收回销毁,严禁流传。
吕留良案至于才告一段落!
吕留良被灭族,冤吗?我认为,吕留良被灭族,既冤也不冤。
说他冤,是因为曾静、张熙这两个无耻文人为了保命,将罪责全推到了已死去四十五年的吕留良身上,换来了一时的苟且偷生;说他不冤,这是因为,自顺治皇帝从龙入关,特别是康熙平定三藩、收复台湾、三征葛尔丹以后,清朝统治者已经基本上有效地控制了全国,饱受战火之苦的天下老百姓们越发渴望和平。康雍两代皇帝顺应了人民群众的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,此时,吕留良的不能与时俱进,仍然大讲“华夷之余发大于君臣之义”,已经站在了历史的对立面上。
其实,早在西汉的时候,儒家就指出,华夏和夷狄二者并没有绝对的界限,谁是真正的华夏,谁是真正的夷狄,不能以地域和血缘来区别,而是要看人民实际达到的道德文化进步的水平。显然,清朝取代明朝是大势所趋,不能因为清朝的统治者是少数民族而忽视清朝统治者对社会、文化的进步,这明显是有失公允的。
雍正为什么要写大义觉迷录?
【任微言卿观点】雍正写《大义觉迷录》,涉及到“正统之争、华夷之辩”,雍正为维护清朝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,挺身而起,主动发声,挟专制统治的政治优势,向根深蒂固的“华夷之辩”展开论战,与反清舆论势力进行正面交锋,意义深远。
让无数汉人纠结的问题——到底何处是中国?“中国”“华夏”一词,自古以来就有多重内涵,而其外延更是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衍变。
上古以至先秦时期,以天子所在地方为“中国”,秦汉以后,随着疆域的开拓、经济重心逐步南移,特别是汉族与周边各族融合的深度与广度的推进,“中国”“华夏”概念的外延也在逐步展开。“中国”“华夏”之外,则为“四夷”。
儒家传统意义上的“华夷之辩”,包含着歧视“四夷”的思想,“内中国而外诸夏,内诸夏而外夷狄”这句古训,浸透着大汉族主义优越感。
实际上,古代“四夷”与“中国”一切恩恩怨怨,都不过是历史上中国这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家事。华夷的分别,从来不是中国与外国的分别;华夷的对立和冲突,从来不是中国与外国的对立和冲突。
传统儒家观念中的“中国”过于狭隘,与历史上汉族与周边各族共同缔造着的大中国的事实不相符合,与今天作为我国专称的中国更不可同日而语,必须摒弃所谓长城外、柳条边是古代中国国界之类的误解和曲解。
清朝初年的正统之争、华夷之辩清朝初兴时,在满人脑海中,“中国”的概念是尊崇的,但“中国”之君不是万世一姓的。无论崛起中的满人,还是身居朝廷、为天下共主的明朝皇帝,都认同事实上存在的大中国框架。
明崇祯十七年、清顺治元年(1644),多尔衮率清军入据北京,顺治帝告祭天地,称大清“兹定鼎燕京,以绥中国”,向天下郑重昭示,正式成为中国的主人。
清朝皇帝十分明确地意识到,他们既“仰承天命”“抚定中华”,即理所当然继大明为“中国”之主。这一历史进程,具有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内向性的古老传统,事实上也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相符合。
但明清易代,在明遗民看来,则是“夷狄窃夺天位”,其严重性岂止一姓王朝的更迭,而是“中原陆沉”,“日月无光”,纲常名教荡然无存,整个社会沉沦于漫漫长夜。
虽然早在康熙时期,就开始了对汉人的怀柔政策,开“博学鸿儒科”、开“明史局”,六下江南亲自祭拜朱元璋,但仍无法彻底消弭根深蒂固的汉民族特别是士人中的敌对情绪,一些人仍在叫嚷“夷夏秩序”,暗中鼓动汉人起来推翻清朝统治,雍正六年(1728)竟发生了曾静策动岳钟琪反清案。
曾静案始末曾静(1679—1735年),湖南省永兴县人,号蒲潭先生,平时授徒为业,性格迂阔,满脑子“华夷之辩”的思想。
曾静应试时,得到大儒吕留良评点的时评文章,见到论述“夷夏之防”等语非常赞叹。曾静派门人张熙专程去浙江吕家访求书籍,因为吕留良已经去世,其家人把吕留良的遗书全部交予张熙,曾静见书中多反清复明之意,愈加倾信。
当时雍正帝正在整治“八爷党”,曾静以为清朝末运已至,顿时上来了一股书生气,派张熙去游说陕总督岳钟琪起兵反清,岳钟琪即具折上奏。雍正帝派人拘讯曾静、张熙,并亲自审理。
雍正认为仅仅惩治一个曾静,并不能改变汉人的反清观念,于是他不循帝王治术的常规,毅然决定利用曾静反清案与“华夷之辩”命题展开一次公开的正面交锋。
雍正将与曾静问答之词,编为《大义觉迷录》,亲自做工作,竟然说通了曾静这个书呆子,曾静亲自到江南地区宣扬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,为清廷做“统战工作”,但是对于始作俑者的吕氏一门,雍正则大加诛戮,吕留良遗著全部焚毁。
雍正《大义觉迷录》的主要观点《大义觉迷录》主要收录关于此案的上谕、曾静的口供和表白心路历程的《归仁录》。
雍正的基本论点和论证逻辑是:满洲人出身是“夷狄”无可讳言也不必讳言,但“夷”不过是地域。汉人所尊崇的亚圣孟子也讲过“舜,东夷之人也;文王,西夷之人也”,如此则“满汉名色,犹直省之各有籍贯,非中外之分别”。
雍正继续讲到,韩愈有言:“中国而夷狄也,则夷狄之;夷狄而中国也,则中国之”,华夏与夷狄的分野不在民族而是以文化定位的。
雍正理直气壮地说:“我朝肇基东海之滨,统一诸国,君临天下,所承之统,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……中外一家之政也”。
雍正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,高标“天下一统,华夷一家”堂堂正正之大旗,对抗挟儒家思想优势的“华夷之辩”命题,志在颠覆大汉族主义自我优越的民族观,争取夷狄与汉人平等的地位。
后话雍正通过辩白,真诚地向臣民表示了对汉人文化传统的认同,有助于化解与汉族臣民的文化隔阂。但汉人两千年的文化传统太根深蒂固了,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收服的了人心的。
《大义觉迷录》除了辩白“华夷之争”,还谈到了当时不少宫廷秘史,这是雍正刊印此书的一个败笔。因为当时的人们普遍怀疑雍正帝位来之不正,他说的话不管正确不正确,人们都不愿意相信。
乾隆继位后,觉得雍正有些矫枉过正了,宫廷密事、君臣对话到处乱传,恐怕会以讹传讹,所以乾隆采取最简单粗暴的方式,直接禁止了这本书,并以“泄臣民公愤”为由,将曾静、张熙处死。
但是乾隆以后,经过百余年融合,广大汉人们在心里上已经趋于认同清朝为“本国”,满汉融合得到了加强。至清中后期,在人民心中,清朝皇帝已经成为名正言顺的“中外一家”的大一统中国之主。
清朝治下各民族从民族认同到统一国家的认同,经历三百年的曲折发展至此终成正果,《大义觉迷录》当时虽然没有达到雍正皇帝的初衷,但至少在臣民心中种下了和解的种子,近代意义上的“中国”在清朝后期正式形成,雍正帝做了特殊贡献。喜欢历史特别是清史的朋友,请@任微言卿 。进入任微言卿主页,还有更多您喜欢的历史。欢迎大家关注、评论、留言、点赞,青梅煮酒,以史会友!
真的是吕四娘杀了雍正皇帝吗?
小说有历史的影子,但不等于历史。经过文艺加工的小说往往比历史更吸引人。当年玄奘大师一个人出发去印度取经的经历,远远不如《西游记》精彩。同样,吕四娘复仇的传奇故事,也比雍正的真实宫廷生活更吸引人。我来叙述一下这段故事的“影子”与历史。
吕家被满门抄斩的大案雍正六年(1728)九月的一天,受曾静的派遣,张熙来到西安,将书信递进正在回署的岳钟琪的轿内,封题称岳为“天吏元帅”(奉行天命的元帅),落款是“江南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”(无主游民,即不承认清朝统治)。
上图岳钟琪画像
岳到署,拆阅书信,吓得“心摧胆裂,发上冲冠”。书信原文已无,但其内容从《大义觉迷录》及有关上谕可以推得:
(1)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。攻击清朝得位之不正,否认其统治的合法性;
(2)数说胤禛是缺德的暴君。攻击胤禛犯有“谋父、逼母、弑兄、屠弟、贪财、好杀、酗酒、淫色、怀疑诛忠、好谀任佞”十大罪;
(3)反清时机成熟。社会陷入了不可解脱的贫富对立。荆、襄、岳、常等地,连年洪水滔天;吴、楚、蜀、粤,旱涝频仍,湖广、广西及粤、赣、云、贵六省百姓,已陷绝境,一呼而起;
(4)策动反叛,推翻清朝。说岳“系岳武穆王岳飞后裔,今握重兵,居要地,应乘时反叛,光复宋、明”。
“逆情”如此严重,岳钟琪愤怒万分,亲审张熙,而张熙宁愿舍生,取义成仁,也不肯透露真实姓名、里居,即使重刑夹讯,也只字不吐。岳钟琪不愿审理此案,担心介入太多,害及自身,遂奏请圣上,欲解张赴京。胤禛安慰他,指出岳的密审,用刑“料理急些了,当缓缓设法诱之”。还替岳设计了诱供手段、言语。岳照办了,对张予以优待,还与之设盟,指天誓地,永不背负。这一招真灵,张很快地上了圈套,供出他们师徒姓名、住址和一切有关人员。
岳钟琪不愧是胤禛的忠顺奴才,将审理情况奏报给胤禛后。胤禛下令逮捕曾静、张熙师徒,押至京听审。酷刑之下,曾静招供:他的反清思想,是误读浙江文人吕留良的著述所致。还招出从吕留良儿子吕毅中家里,得到《吕晚村文集》并《备忘录》,以及与吕留良弟子严鸿逵、沈在宽来往投授的过程。上图吕留良画像
此案的处理上,胤禛宽恕了曾静,严惩了死去40多年的吕留良及其亲友。胤禛的解释是“若非因曾静之事,则谣言流布,朕何由知之,为之明白剖析,俾家喻而户晓……在曾静亦未为无功。”胤禛果然宽释了曾静、张熙,让他们作文批判吕留良,到各地演讲,宣扬“圣德同天下之大”,“本朝得位之正”等等,还谕令后世子孙,不得以任何借口,戕害曾张二人(弘历即位,立斩二人)。
对著书立说的吕留良,则恨之入骨。胤禛说,吕留良“悍戾凶顽,好乱乐祸”,“著邪书,立逆说,丧心病狂,肆无忌惮”,罪恶甚于曾静。又说:“曾静只谤及于朕躬,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圣德;曾静只谤讪,由于误听流言,而吕留良则出自胸臆,造作妖妄;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,有较曾静为倍甚者也。”看来,在胤禛的眼里,思想上的叛逆,比具体行动更为危险,而要彻底清除思想上叛逆的根源,不能不抓住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靶子来大作文章。在读书人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吕留良,就成了胤禛大作文章的靶子,因而对吕留良的惩治也格外严厉。
雍正八年(1730)十二月连降谕旨,将吕留良及已故儿子吕葆中戮尸枭示,儿子吕毅中斩决,吕家孙辈人数众多,全部发往边地为奴;所著文集、诗集、日记等,尽行烧毁;弟子严鸿逵及沈在宽凌迟处死,刻书人及与其交往者全部问斩,此狱被杀者百余人,流放者数百人。
小说的演绎:吕四娘复仇吕家罹难时,适值吕葆中的女儿吕四娘外出,惊闻阖家抄斩,悲愤万分,当即刺破手指,写下“不杀雍正,死不瞑目”的血书,立志为父、祖报仇。
那年,她才14岁,独自一人从浙江来到少林寺,拜一名僧为师,学艺练武。她很刻苦,每天闻鸡起舞,不管白天黑夜,严寒酷暑,总要站桩练功;也不管风天雨天,总要坚持打拳踢腿,舞刀弄棒。一晃4年过去了,少林长拳、飞檐走壁、空中飞剑等,样样武艺,精到超群。有些传奇说先去了黄山,后去了天台山,还有拜师明朝朱姓“独臂神尼”之说。
一天,四娘正在练鞭,突然飞来几枚飞镖,只听噹噹作响,被抽落坠地;接着又飞来几把飞刀,四娘纵身上梁,飞刀把把落空,低眉一瞧,原来是师傅在旁。师傅对她说:“你武功已练成,报仇时机到了。”后来,她泪别师傅,赶至京城,很快地摸清了胤禛在圆明园(一说为“乾元宫”,而紫禁城和圆明园无此地)内的居址、通往途径。
一天晚上,她乔扮为宫女,潜入宫中,静候一株古柏上,见一太监打着灯笼,带领宫女向寝宫走去,她轻轻落地,紧随其后,混入寝宫外室听命。胤禛进来,一眼看中四娘,四娘故作顺从,频频向胤禛敬酒,灌得胤禛大醉,晕卧在床。四娘见状,拔出利剑猛刺,割下头颅,用锦布裹好,提着首级而去。后来,大内传出消息,说胤禛暴死,又说胤禛无头,不得已铸个金头,完尸下葬。
这则故事,绘声绘色,流传很广,听起来像是真事。但是,同其它胤禛被刺的传说一样,都不可能是真的。当然,均非史实。
吕留良文字案,在雍正朝乃至清王朝都是一桩特大的案件,又遇上胤禛这样精明的君主,审理便更加严密,不可能有疏漏,即或有之,也难逃以缉捕著称于世的浙江总督李卫之手。况且圆明园警跸森严,内有护军营护卫,外有巡防营梭巡,园内殿堂座座,哨卡林立,怎么能想象出一个弱女子会接触上鼎鼎尊严的皇帝呢?
所谓胤禛被刺,无非是人民在想象中并借助想象的力量,去反对邪恶、反抗压迫的美好愿望而已。就像《九品芝麻官》中的街头说书人绘声绘色的讲述“包龙星被十几个壮汉强奸”而大众鼓掌欢迎一样,反映了一种情绪和民心,而和事实相去甚远。





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