引言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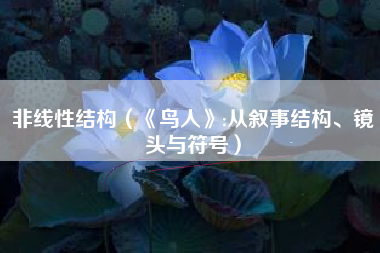
雷蒙德·卡佛被誉为“美国的契诃夫”,也是美国少见的“艰难时世”的观察与反思者,他的一生生活困苦,为了养家糊口,在频繁更换的工作中奔命,也正因如此,他击碎了“美国梦”的虚幻泡沫,让人们了解到真实的美国不仅仅是富人的天堂,也是穷人的地狱。同时,他极尽客观、流水账式的写作方式,既达成了契诃夫“越客观、越让人印象深刻”的小说定义,也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极简主义小说。短篇小说中频繁使用的开放式结局,更是成为映射读者内心的一面镜子,引发出不同的思考。
远在千里之外,出生在拉美的亚利桑德罗·冈萨雷斯·伊纳里多,有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,却因为家庭变故,陷入生活的挣扎,被学校开除知乎,他成为一名水手,世界各地旅行。他自己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:“那些年的经历磨练了我,让我明白了探寻不同事物的价值所在。”加上大学毕业后的摇滚DJ经历,直接影响了他的电影导演之路。
拉丁美洲做为魔幻现实主义的爆炸之地,既诞生了加西亚·马尔克斯《百年孤独》这样的文学巨著,也是曾轰动一时的动画电影《寻梦环游记》的灵感来源,这种复杂的民族文化,对亚利桑德罗·冈萨雷斯·伊纳里多同样影响至深。
电影《鸟人》是一部充满魔幻色彩,却具有深刻现实主义电影,亚历桑德罗·冈萨雷斯在绚丽多姿的好莱坞泡沫中,像雷蒙德·卡佛一样,将目光转移到逐渐被人淡忘的小人物和事物的另一面,以此,做为对美国文化的补充和反思。
同时,整部影片采取了亚历桑德罗·冈萨雷斯惯用的多线性叙事结构,近乎一镜到底拍摄手法,让人惊叹于导演和演员的配合与实力。该片上映之后,即斩获了第87届奥斯卡,包括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在内的四项大奖。
一、多重互文叙事结构
电影《鸟人》讲述的是男主人公里根是一名已经过气的好莱坞演员,过去的他,凭借着飞鸟侠这样一个超级英雄而受到观众的喜欢和崇拜,后来,因为一场小矛盾引发的争吵,和自己的妻子离婚,事业也一落千丈。走在人生低谷的里根,迫切的希望通过在百老汇上演一场舞台剧来挽救自己的演艺事业,重获大家的关注和喜欢。
但是,一切却远非想象中的那样顺利,因为不满自己的合作对象,他眼睁睁看着屋顶上掉下的道具将他砸伤。重新换来的合作对象迈克,虽然演技得到认可,却是一个在现实和舞台上随意发挥、难以控制的角色。同时,自己的女儿因为毒瘾,刚刚从戒毒所出来,在自己身边做助手。爱情、事业和亲情混乱的交杂在一起,考验着里根的人生。
影片采取了多重互文叙事结构,“互文性”按照法国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的说法:每一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镜子,每一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,相互参照,彼此牵连,构成巨大的开放体系。
随着电影的发展,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和真实人物的经历完成了“字到图”的转化,对于这种转化,吉尔·内尔姆斯的《电影研究导论》认为:狭义上说,互文是一部电影与另一部电影直白或隐晦的参照方式,广义上来说,是一部电影与另一个文本之间的内在或外在联系。
对于《鸟人》来说,主角迈克尔·基顿的真实经历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素材,这是他从2008年以来首次担任影片主演,上一部主演的电影是由他自己主导,这部影片和迈克尔·基顿《第6场》的背景高度相似。而《鸟人》中的主角里根,拍摄了前三部《飞鸟侠》之后,拒绝了第四部的拍摄,从此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一落千丈,这是对迈克尔·基顿好莱坞生涯的映照。
里根的角色,在一定程度上,也是小说家雷蒙德·卡佛投射,这个被美国保守主义者视为“异类”的人。现实中的雷蒙德·卡佛不喜欢饮酒,自己的老婆是高中老师,他曾经说:“发现生活中有比写书更重要的是,对自己是一种折磨。”心想事不成,被生活和文学分裂开的人生,这些我们都可以在影片中里根的身上看到。
互文性所具有的双重涵义:暗合和悖离,对电影中的里根和现实的迈克尔·基顿来说,暗合的是他真实的生活经历和困惑,悖离的却是他凭借此片重获男主身份。
影片中,另一个具有“互文性”关联的是改编自美国著名小说家雷蒙德·卡佛短篇小说《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》的舞台剧,这场“戏中戏”,采取了和原著相反的叙事结构,利用倒叙的方式,呈现在观众面前。在雷蒙德·卡佛的同名短篇小说里,开始就提到了艾德自杀,争论也是围绕艾德自杀证明爱情开始。在电影中,艾德自杀却放在了舞台剧的最后,自杀虽然暗合了小说的情节,却悖离了原有的意义,引发了人们另一层面的思考,同时,这也是对剧中人物里根处境的映照,起到了三重作用。
多重互文叙事架构,强化了影片中人物的生存状态,加强了真实度,赋予了影片更多的思考,也让我们对故事和人物有了更复杂的认知。
二:长镜头和象征隐喻符号的运用,体验魔幻现实主义带来的极致“另类美感”
在《鸟人》中,导演亚历桑德罗·冈萨雷斯采用了大量长镜头,让人体验到“一镜到底”技术所带来冲击和酣畅的观影快感,也被摄影师高超的拍摄技术和演员的表演功底所折服。
法国电影理论家巴赞认为:长镜头是保证电影真实性的重要手段。
长镜头提供了时空上的连续性,看不出任何拼接的痕迹,让影片具有了不容置疑的真实性。
在《鸟人》中,镜头从里根悬空打坐的开始,跟随着他的移动而运动,同时,变换着的镜头角度,完成了蒙太奇镜头所承担的“人物面部表情捕捉”的任务,在观看过程中,我们的眼睛替代了镜头,呈现出一个“上帝视角”,就像是一个旁观者,见证着人物的表情、动作,对人物的情绪也有了更直观的感受。
同时,鼓点的音乐和实时的特写镜头的冲击,避免我们陷入到眩晕和枯燥的观影过程。
当我们跟随里根从房间出来去参加排练时,镜头围绕着坐在方桌上的四个人物旋转两周时,明显感觉到一种眩晕感,镜头适时切换到里根的面部表情上,阻止了眩晕感的继续,让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表情所引发的猜测上来。
类似的运动长镜头充斥了整个影片,加上频繁出现的鼓点打击乐,既保证了影片的真实性,也让我们对人物的生存状态有了一种更真实的体验。
从拍摄的范围看,整部影片的长镜头,大多是在一幢话剧院的建筑里完成,堆满化妆品、镜子和床的小房间、狭窄的几乎只能容忍一人走动的通道,昏暗的灯光,都和外面的世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,封闭和包容、局促和自然,让我们不禁思索里根身体在哪,心又在哪。
事实上,里根就像我们从镜头中感受到的一样,对生活和事业充满了眩晕的挣扎和压抑的局促。
除了镜头所带来的美感,影片中还充满了象征隐喻的符号。
影片开始时,一个燃烧的物体从天空陨落,紧接着镜头快速切切换成躺在沙滩上的海洋动物尸体,它们是对希腊神话中伊卡洛斯的隐喻。
在希腊神话中,代达罗斯用蜡和羽毛为自己的儿子伊卡洛斯制造了羽翼,两人借此逃离克里特岛,临行前,父亲告诫他:“必须飞在半空中,不要飞的太高,不然会因为靠近太阳而着火;也不要飞的太低,羽翼沾水,你会被拽进大海。”骄傲的伊卡洛斯不听劝阻,越飞越高,最终跌落海中。
里根一直将自己标榜为“伊卡洛斯”式的人物,它象征的是一颗不向现实屈从的心,相对于普通民众和记者、好莱坞的规则来说,里根是弱势的,也是引人同情的,他想要证明自己,却总是被人误解和打击,成为了加缪笔下“西西弗斯情结”的战士。对他而言,要么违背真实的内心,屈从于外界种种规则,成为一个无知却充满魅力的“上帝”,要么成为一个为艺术和哲学献身的殉道者。
在影片中,里根被分裂开,一个是已经获得公众认可的“飞鸟侠”,另一个是自己真实的内心。他从好莱坞来到纽约百老汇,本意上就是想要摒弃过去的名人身份,成为一个获得认可的演员。所以,飞鸟侠就像一个标签一样贴在他的身上,想撕却撕不掉,在他追随自己演员梦想的路上,不时出现打击他、诱惑他。
无论是伊卡洛斯还是飞鸟侠,还有里根想象的御空飞翔,都让我们见到了建立在现实主义上的魔幻,而长镜头所带来的上帝视角,更是将这两种状态推向了极致的美。
三、多重审视剧中人物所折射出的人生困境
影片中,每个人物都折射出了不同的人生困境,同时他们的人生困境因为各种关系的连接而揉杂在一起,产生了摧毁性重构的力量。
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将人生分为八个阶段,每个阶段都有需要解决的冲突,对于里根来说,他处在成年期,面临着生育和自我专注的冲突,中年危机的典型特征恰恰是急需别人的认可,来获得自我认同。
对里根来说,事业一落千丈,因为将崇拜和爱情混为一谈和妻子离婚,女儿因为吸毒进了戒毒所,一次从洛杉矶到纽约的航班上,他和乔治·克鲁尼同机,飞机遇到了强烈风暴剧烈震动,唤醒了他那颗已经被社会边缘化的孤独的心,他忽然想到,如果现在飞机出事,自己就成法拉·福塞特,报纸上不会提到任何关于自己的消息,因为他们都去报道迈克尔·杰克逊的死亡。
自我专注让他忽略到了关心自己的女儿,不惜卖掉留给女儿的房子来拍摄舞台剧,以便获得公众的认可和尊重,满足自己的自恋心理。
可是,却总是被外界所误解,被娱乐记者选择性的解读,被自己的搭档迈克当作笑话,被批评家迪金森贴上无知的名人标签,被女儿嘲笑,种种的一切,都在诉说他已经是一个过时了的名人,他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这些外在的压力。还有自我内心的冲突,是选择投降重回过去的生活,还是不顾一切的去追寻真实的自己。
对迈克来说,他是一个不能见光的演员,自以为是却缺乏安全感,他和萨姆玩真心话大冒险,每次都是选择真心话,不敢选择大冒险,他带着虚伪的面具应对现实生活,只能在舞台上才敢表现出真实的自己。
莱斯利则从小女孩时期就梦想成为演员,在百老汇舞台上演出,成为一个有自尊的女性,可是,却被迈克当着八百名观众的面羞辱,一直被当作一个小女孩去看待。
对萨姆而言,自己的父亲里根从不关心自己,只是被不断的告知自己是特别的,事实上,对她而言,一直是脆弱、无助的。正如埃里克森所言,她感受不到自身的存在,只能通过对生活的背叛、用近乎燃烧自己生命的方式去证明自己的价值。
对他们每个人而言,处境都是完全不同的,可是所面临的人生困境却是相同的,他们都想要通过自己的方式证明自我的价值、证明自己是一个被值得尊重和关注的对象。
只是,就像自卑和自负只不过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一样,他们每个人都面临着正反两面的选择。对里根来说,要么选择妥协,成为一个无知却高高在上的上帝,要么成为一个陨落大地的伊卡洛斯;对迈克来说,是选择继续逃避,在戏里面演绎真实的人生,还是勇敢面对,在生活中重塑自我的价值;对莱斯利来说,是选择正视别人对自己的评价,勇敢打破,还是被生活击败,回到小女孩的状态;对萨姆来说,是选择向父亲坦诚自己的脆弱无助,还是继续以极端的方式来隐藏自己的心思。
一幕舞台剧,将他们所有人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,产生了不同的化学反应。萨姆和迈克,相同的处境,让他们彼此相拥,彼此治愈,莱斯利也因为舞台剧的大获成功得到了观众和同行的认可,而对于里根来说,这场舞台剧成为了一场寻求真实自我的过程,虽然最后仍然不可避免的被贴上了“超现实主义”的标签,最后的结局无论生与死,他都获得了一次重生。
事实上,对我们每个人而言,不管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,我们都会面对属于自己的困境,不被理解,不被尊重,让我们时刻感受着自我与外界冲突所带来的异化感受。
当我们面对这些困境时,是选择妥协还是坚守,或许就像是片中所提供的开放式结局,没有确定的答案。实际上,我们需要终其一生,去寻找那个在阶段性的困惑中总是迷失的自己。





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