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我们季候的诗歌:史蒂文斯诗文集》 [美]华莱士·史蒂文斯著 陈东飚、张枣译 陈东东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华莱士·史蒂文斯(Wallace Stevens),1879年10月2日生于宾夕法尼亚雷丁,1955年8月2日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逝世。尽管他在求学时就在《哈佛呼声》(Harvard Advocate)上投稿,但获得广泛知名度则是在哈里耶·蒙罗(编辑,学者,文学批评家,艺术资助人)将他的四首诗收入《诗歌》杂志1914年战时特刊之后。他的第一本诗集《簧风琴》(Harmonium)出版于1923年,随后问世的是《秩序的观念》(Ideas of Order,1936年),《弹蓝色吉他的人》(The Man with the Blue Guitar,1937年),《一个世界的各部分》(Parts of a World,1942年),《运往夏天》(Transport to Summer,1947年),《秋天的极光》(The Auroras of Autumn,1950年),文论集《必要的天使》(The Necessary Angel,1951年),《华莱士·史蒂文斯诗集》(The Collected Poems of Wallace Stevens,1954年)和《遗作》(Opus Posthumous,初版于1957年,新修订校正版于1989年)。1949年获耶鲁大学博灵顿诗歌奖;1951年以《秋天的极光》获国家图书奖的诗歌奖;1955年以《华莱士·史蒂文斯诗集》第二次获得此奖以及普利策诗歌奖。从1916年起加入哈特福德意外事故保险公司,1934 年任副总裁。 ·译者简介 陈东飚(1967— ),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,20世纪90年代以来翻译的文学与人文著作有纳博科夫《说吧,记忆》,《博尔赫斯诗选》,埃利•威塞尔《一个犹太人在今天》,艾兹拉•庞德《阅读ABC》,《华莱士•史蒂文斯诗选》,巴塞尔姆《60个故事》《40个故事》,迈克尔•杰克逊《舞梦》,帕斯《泥淖之子》,《博尔赫斯与费拉里对话集》,麦卡勒斯《伤心咖啡馆之歌》,马内阿《囚徒》,凯鲁亚克《达摩流浪者》,《玛丽安•摩尔诗全集》等。 张枣(1962—2010),诗人,德国图宾根大学文哲博士,著有诗集《春秋来信》。他长期寓居西方,在大学从事汉语诗学及世界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,2007年以后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和新闻传播学院教授。谙熟英语、德语、法语和俄语,翻译过里尔克、策兰、希尼、夏尔等诗人的作品,并主编了一部德汉双语词典。身后出版的著作有《张枣的诗》《张枣译诗》《张枣随笔集》及他的博士论文《现代性的追寻:论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》(由亚思明从德语译成汉语)等,2021年,又出版了五卷本的《张枣诗文集》(颜炼军编)。 ·内容简介 华莱士·史蒂文斯是20世纪美国著名现代主义诗人,美国国家图书奖、普利策诗歌奖、麦克阿瑟奖获得者,被评论家称为“诗人中的诗人”。史蒂文斯大学时就读于哈佛,后在纽约法学院攻读法律。1903年毕业后,先在纽约干了十几年律师工作,1916年进入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意外事故保险公司,1934年出任公司副总裁,直到退休。他的兢兢业业,他的条理分明,他丰富的内心和隐忍的语言分寸感,不仅打理了必要的日常事务,也成就了诗歌这个超级虚构的美丽事业。他使我们相信,诗歌就是一种因地制宜,是对深陷于现实中的个人内心的安慰。史蒂文斯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坚持了浪漫主义以来想象力的崇高,而且还在于他坚信现实世界之事实性和事理性的崇高。现实就是想象,世界不自外于诗歌,词就是物,写作就是生存,而生存,这个“堆满意象的垃圾场”,才是诗歌这个“超级虚构”的唯一策源地。史蒂文斯一生追溯的诗意,就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的。其一贯性和不屈不挠的表达意志,让人惊叹。诗人心智之丰满稳密,处理手法之机敏玄妙,造境之美丽,令人艳羡和折服。 本书由诗人陈东东选编,翻译家陈东飚、诗人张枣合译,精选史蒂文斯87首传世诗歌,并独家收录诗人张枣翻译的《徐缓篇》全篇、陈东飚翻译的文论集《必要的天使》,从中一窥史蒂文斯的诗艺和诗歌精神。 ·序言 “世界是一种力量,而不仅仅是存在” 文 | 张枣 华莱士·史蒂文斯(Wallace Stevens, 1879—1955),1879年10月2日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雷丁市。大学时就读于哈佛,后在纽约法学院攻读法律。1903年毕业后,先在纽约干了十几年律师工作,1916年进入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意外事故保险公司,1934年出任公司副总裁,一直干到退休。在这个公司的高职位上,他的兢兢业业,他的条理分明,他丰富的内心和隐忍的语言分寸感,不仅打理了必要的日常事务,也成就了诗歌这个超级虚构的美丽事业。他使我们相信,诗歌就是一种因地制宜,是对深陷于现实中的个人内心的安慰。 史蒂文斯大学时代已开始写作,24岁时,他的四首作品得以在美国著名的文学杂志《诗歌》上发表,并获该杂志的战时诗歌特辑奖。这些使得他的同事和客户对他稍稍有点另眼相看,也多了一份对他的尊敬,但在文学专业圈里,基本没有人关注他,更没有人想到,一个未来的诗学大师,一个企盼承传美国诗歌传统,在新时代重新发明所谓“美国崇高”的双面人,正在悄悄地坚韧地工作着。 1923年,43岁的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《簧风琴》(Harmonium),十几年后才出版第二本诗集《秩序的观念》(Ideas of Order, 1936)和组诗《弹蓝色吉他的人》(The Man with the Blue Guitar, 1937),1950年出版《秋天的极光》(Auroras of Autumn),1955年,他76岁,因癌症屡次接受住院治疗,嗅到死之临近,才不情愿地出版他的全集。可见他是一个大器晚成的诗人,一个耐心的循序渐进的大师,一个羞于诗歌的外在名望而只沉溺于“语言之乐”的奇异的享乐主义者,一个精致的浪费者。 在早一些的诗里,史蒂文斯似乎爱用两种颇有差别的语式说话,一种偏向讥讽,甚至在不少人的感受中,是恶意,这类语式的诗一般显得怪异,奇想迭起,用词忽儿粗俚,忽儿艳俗,一种雅皮士的姿态讥讽自身的出格和与世界的格格不入,因而在元诗层面上也就故意摆出反诗的派头,来渲染对温雅守旧的写作的不满。另一种语式是抒情而崇高的,同时洋溢着康德式的明朗圆润的理性,散发出西方古老的诗哲同源的明晰观念,这类作品有《黑的统治》《雪人》《坛子轶事》《看一只黑鸟的十三种方式》《胡恩宫殿里的茶话》《我叔叔的单片眼镜》《星期天早晨》《彼得·昆斯弹琴》《十点钟的幻灭》,等等,它们一般更受学院批评家如布鲁姆(H.Bloom)、文德乐(H.Vendler)、米勒(J.H.Miller)、克尔莫得(F.Kermode)等人的关注,也成了他们用以演绎自己诗学理论的经典原本;在世界文学范围内,这类作品似乎也流传更广,一般也被读作是与史蒂文斯晚期创作,或者说典型的史蒂文斯,共生同构的一部分。 史蒂文斯坚称想象力是对诸神隐遁后之空白的唯一弥补,是人类遭遇世界时的唯一可能的安慰,“上帝即想象力”(《徐缓篇》)。当想象力作用于现实(reality)时,现实便从其单纯的事实显象中脱颖而出,一跃成为“猛虎,可以杀人”,成为“狮子,从天空跑下来饮水”,成为鲜活的动力,成为我们的紫气缭绕的气候: 莫以为我在紫气缭绕中穿越 所谓极至的孤单并降落西天, 我就会少了一点我自己。 我胡须上亮闪闪的膏药, 不绝于耳的颂歌,大海在我内部的 潮涨潮落,这些不算什么吗? 我的心境下着金色的香油之雨, 我的耳中回旋着颂歌的听觉, 我自己就是汪洋大海的罗盘: 我自己就是那个我漫游的世界, 我的所见所闻皆源于我自身; 那儿,我感到我更真实也更陌生。 可见,想象力作为主体,穿透万物,占据现实,成为“汪洋大海的罗盘”和世界的慧心(mind),使生命趣味盎然,同时也拓展了主体的真实,给主体带来获得真实的陌生的惊异感。同样,《基围斯特的秩序观》一诗里,那个用歌声缔造大海和世界的女歌者,也庆典似地宣告“世界从来就是她唱出的世界,/对她而言,绝非他物”,如此世界,因为吐纳着“更恰切的微妙,更清晰的声响”,才秩序井然,因为有着“香门之词,隐约被星空烘托”,才令人迷醉,也才值得栖居: 罗曼·费定南兹,可否告诉我 这是为何:当歌声结束,我们 回城,那些荧灯,那些 停泊的渔舟的灯火,面对 空中跌落的夜色,竟然 把握了夜,分配了夜?竟然 摆布出火树银花,安排, 加深,甚至迷醉了夜? 读者应该留意的是,史蒂文斯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坚持了浪漫主义以来想象力的崇高,而且还在于他坚信现实世界之事实性和事理性的崇高。“世界的迷人之处正是世界本身”(《徐缓篇》),而世界本身就是最终的价值和诗歌(想象力)最高的理由。尽管现实能够升腾跃进成“秩序的激昂”,诗歌却不是现实的对立物,而是它的内蕴物,也就是说,史蒂文斯对想象力的一切赞颂,都可以毫厘不差地被换置为现实本身,因而,现实就是想象,世界不自外于诗歌,词就是物,写作就是生存,而生存,这个“堆满意象的垃圾场”,才是诗歌这个“超级虚构”的唯一策源地。史蒂文斯一生追溯的诗意,就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的;长篇组诗《朝向一个至高虚构的笔记》和《弹蓝色吉他的人》,连同他的经典短诗和诗学文论,无与伦比地聚焦和演绎了这个迷人的核心主题。其一贯性和不屈不挠的表达意志,让人惊叹。诗人心智之丰满稳密,处理手法之机敏玄妙,造境之美丽,令人艳羡和折服。 资料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编辑:段鹏程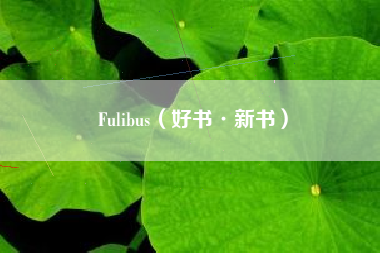
正文
Fulibus(好书·新书)
由于无法甄别是否为投稿用户创作以及文章的准确性,本站尊重并保护知识产权,根据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》,如我们转载的作品侵犯了您的权利,请在一个月内通知我们,请将本侵权页面网址发送邮件到,我们会做删除处理。





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